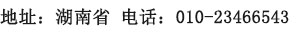拉康心理
作者:让-雅克.格罗格(Jean-JacquesGorog)
译者:潘恒
“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这个三元组不只是在拉康的连续建构中的一种理论性书写或者公式化元素。这三个字母代表着一种思考我们所是的“言在”之方式。自始至终,它们作为其整个教学的背景,有点像阴和阳组织了中国思想那样。首先要注意的是,必须要计算到3。这是一个确定的三元系统;必须要考虑到这点的重要性,就像将“三节拍系统”音乐区别于“二节拍系统”音乐那样重要。三元思想总是难以同时运用的,以致于描述事物时的自然倾向将自发地缩减为一个元素与另一个元素间的二元对立。就我所理解的中国思想而言,似乎其方法是反过来的;比如,中国思想从2出发并以多种方式在对立面的链接中引入3。在拉康那里,这一三分法是个常量,以致于他所阐述的每句话几乎总是包含这三个范畴。无疑,这是显然是力求做到精确,不过同样这无疑是使阅读变得困难起来的因素之一。
举个例子,拉康的一句话:爱就是将“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提供给某个“并不接受它”的人。在这一爱的定义中,三个范畴都呈现出来并交织在一起。简言之,首先,爱是想象性的;“提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属于象征界;而“某个并不接受它的人”代表了与拉康用实在界所指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逆向来处理这句话,就相当容易理解它了。显然,如果一个男人——我用性别化来处理它,以便使论证变得容易,我将在后面说明它具体是怎样的——将他所拥有的东西,比如钱,给予一个女人,以便博得她的好感,那么我们严重怀疑这是爱情。那么,现在,他将与其所没有的东西一样神秘的这个事物提供给她,那么她怎么接受呢?我们后面再说。
两个框定拉康整个教学的题目证明了三界这一主题的恒常性。年,召开了题为RSI会议;这恰好先于其教学;-年,其最后的几个讨论班之一也题名为“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
即便后来精神病使他清晰地区分这三个范畴——首先可见的想象性灾难,是由在实在界中与被除权弃绝的象征界的相遇所引起的,那么将这三个范畴的配置运用于神经症在其教学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在这里,精神病起着支撑作用。俄狄浦斯情结假定了弗洛伊德在连续的几个时刻中所建立起的结构。我们知道这几个时刻:对母亲的爱、父亲所带来的阻碍,然后根据个案的情况,产生了对父亲的爱或认同父亲。在这里,根据是否具有男性器官,性别得到了清晰地划分:对于女孩来说,产生了对父亲的爱;对于男孩来说,认同于父亲,并在母亲之外寻找另一个女人。换言之,无论性别如何,都具有同一个开端,因为小孩自认为具有阴茎。然后,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运气,孩子获得了性别差异,于是建立起一种不对称性。后来,弗洛伊德和拉康在有一点上截然不同。对弗洛伊德来说,女性化道路中充满困难,因此是复杂的、意外性的且神秘的;男孩的道路则更为简单。然而,拉康却认为恰好相反,男孩的历程是更困难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审视RSI的分类给弗洛伊德式的诸多情结所带来的好处。
这始于年的?家庭情结?一文。这篇文章描述了弗洛伊德已描述过的三种情结——断奶情结、侵入情结与阉割情结。断奶情结是原初客体的丧失,指的是乳房而非母亲的丧失。我们知道这是关于“丧失的客体”的模型,后来也成了拉康式的对象(a)的模型。对拉康来说,断奶是实在界的,不过在孩子丧失乳房的时刻,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乳房。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已经丧失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因此,对于已丧失的客体,他从来不曾拥有过。在后续的各类定义中,比如作为不可能性的实在界,或者总是返回同一地点的实在界,亦或图书馆中不在其位的书籍,等等,都与这原初丧失相吻合。
侵入情结处于第二时期,是想象界的。即便关于侵入情结的诸多前提假设已处于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中,也还是这一时刻首先构成了拉康的发明。然而,弗洛伊德式的自恋并没有在对自身的爱中区分出对自身形象的爱与那克索斯神话所蕴含的致死维度——因为那克索斯因够不着自己的形象而毁灭自己。与类似者之间的关系被构想成一个必要的时刻,而镜子阶段是其关键时刻。在镜子阶段中,所涉及的正是在对自身形象的识别(认可)中的言语型干预经验。不过,事实上这一时期并不单一,还存在许多与类似者对质(对照)的时刻;在这些对质(对照)中,重要的是从逐渐获得的自身形象中得到支撑。对于这一点,拉康借用了米兰妮.克莱因的观点;在克莱因看来,继最初的破碎身体之后的身体“统一体”意味着引入了“死亡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克莱因来说这一时期是躁狂-抑郁型的。如果孩子没体验过统一性,他就无法理解体会任何破碎性。拉康后来根据这一既定的理由评论了破碎的身体。在这里,拉康完全是弗洛伊德式的,并且强调只有根据退行的思路,才能设想精神分裂症的破碎身体;并且这种退行是拓比性的,意思是其所涉及的并不是返回童年期。因此,与身体的关系,即统一体与并行的死亡维度(包括杀死他者以及主体自身的死亡),通过想象界被构建起来。可是,只有在与言语的关系中,这一想象才得以构成。
必须要理解到不存在单独的想象界,语言的补足是必要的。实际上,通过语言对孩子的决定作用,“他者入侵”这第二时期可以细分为二个时刻。这里,可以用弗洛伊德小外孙的fort-da游戏作为参照。多亏了一个可以被他先抛出去再拉回来的卷轴,他使自己成了母亲在场/缺场的主人。总之,他用不着母亲的永久在场了。这正是拉康所说的“象征界的实际入口”。
最后,还存在一个第三时期,标志着阳形功能、俄狄浦斯与阉割的进入。此时,对于每个人而言,从定义了人类关系的两种模式出发,即认同与对象选择,性别差异得到了规定。这一时刻被假定为象征性的时刻。
问题在于:由于这一秩序混合了发展与结构,因此它仍然是复杂的。我的看法是:如果语言是一个无法厘清源头的既定集合,那么“象征界、结构”与身体形象不同;与象征界或结构相反,身体形象,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构建于且明确于想象性的时期。实际上,这三个发展时期并不是相继构成的,它们相互交织。大家都知道婴儿并不依照可推理的学徒期运作。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可能先会说一个完整句子,尔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再进步。它通过极高的敏锐度理解了一些元素,但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期限、时间等。与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相反,这里并不是语言的运用成了难题,而是想象界难住了它。理论上来说,一个词可以指涉多个事物并不会使其灰心,但是将这定位于时间和空间中则给它带来了诸多其他困难。
性别差异的问题也同样与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交织在一起。拉康选择还原每一范畴所具有的特殊性。与类似者的关系应当清晰地与性别差异的问题区别开来,但同时不能忘记身体的实在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都必须妥当地安置RSI。“言在”诞生于语言的浴室中,实际上是象征界的浴室中,每一个词语都指向另一个词语;非常不利的是,言在必须利用其有生命的身体以便幸存下来,这就是实在界。多亏了其身体形象的捕获,它实现了这点。身体形象是一个根本性范畴,但其重要时常被忽视,因为幻象(错觉)与之相伴而生。可是,想象界虽然具有欺骗性,不断地误导我们,但是它对于辨认出方向以及赋予世界以秩序而言都是极为必要的。
只有清晰地区分这些范畴,才能理解神经症的临床。现在,我将更详细地讲一讲。在整个20世纪期间,神经症已变换了意义。与精神病主体不同,神经疾病的病人,也就是所谓具有好的精神健康状态的正常主体,已成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撇开他仍然痛苦且不断抱怨之外不谈。这就是症状。这个词出自医学,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于我们的领域,或者依据拉康后期的注释,也就是离我们更近的注释,症状变成了“圣状”。正是症状定义了神经症。
症状仍是一个没有得到澄清的问题,且与口误、过失行为、妙语和梦一起,它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无意识的诸多形成物中。不过,无疑拉康后来偏爱将它单放起来,因为症状具有不同的地位,相对于其他无意识形成为的瞬时地位,它具有永久性。此外,尤其困难的是将瞬时的内容与具有永恒特征以及某种惰性的部分很好地分离开来。这将涉及到无意识所产生的分裂主体与具有一段期限的欲望之间的差别。
我们可以立即发现症状的分布是介于象征界(具有瞬时维度,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具有持续性的自我(即想象界的惰性)以及对身体的参照(癔症证明了其实在性)之间。症状本身被置于RSI之间。
其实,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中,症状首先是癔症性的,即妥协形成物。弗洛伊德说:症状是多元决定的。在这种多元决定中,我们同样能注意到不同范畴的作用。实际上,症状同时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1)纯粹的能指元素,拉康用“单一特征”来处理它们。它涉及到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东西,比如,其模型可以是杜拉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咳嗽。不过这一咳嗽具有负面价值,因为它涉及到父亲的疾病,被弗洛伊德解释为父亲阳痿的标志。因此,与人们通常所想象的恰好相反,这不是对父亲的一个理想特征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特征是与有缺陷的父亲之间关系的象征。
(2)癔症同样也涉及到一种拉康所说的想象认同,即欲望对欲望的认同。举个弗洛伊德所给出的例子:在女子学校中,一个女生收到男朋友的分手信后哭了;那么其他女生出于这种认同也哭了。此外,杜拉个案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对k夫人欲望的认同(k夫人与杜拉的父亲有关系),也就是说欲望这个阳痿的男人。弗洛伊德并没有立即觉察到这点。对此,应当安置这种模式,症状可以出现在其之下。她还借用了k先生(k夫人的丈夫)的套路。k先生应当给她提供关于“什么是一个女人”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k先生与k夫人有关系,而k夫人对于杜拉来说掌握着“神秘的女性存在”之秘密。
(3)根据弗洛伊德,一种身体性的烦恼(困难),“身体被牵连进来”是必然的。它属于实在界,并且拉康用每个人与自身身体间所维持的享乐关系来处理症状与身体间的关系。仍可以用杜拉个案来加以说明。显然在其中存在着产生咳嗽的实在性问题,并且后来和父亲的关系维持了这一问题。之后,还有圣母像,在圣母像前,杜拉陷入陶醉中;这不只是一副被爱慕的画像,还是女性存在、享乐出现的地方。
正是上述三种认同建立了癔症症状;它应当得到精神分析式的处理。不过,不应忘记这构成了其存在。我们可以缩减其症状的病理性外延,不过使其消失会使主体的存在一同消失,这是任何言在理应拒绝的。
强迫神经症是癔症的一种“方言”。它同样蕴含这三种范畴的作用,不过却牵连着在“阳形”介入方式上的细微差异。
其实,在女性方面,「不具备代表“阳形”的器官」这一事实导致了癔症形的解决方式,即便这保留了两种可能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器期”后,第一幼儿性欲理论涉及到这样的念头:通过与男孩进行对照,在女孩觉察了自己缺了这一器官时,她认为自己丧失了器官。不过拉康补充了这点:女性位置同时蕴含着别的,也就是她从不曾拥有过这一器官。这既使她在面对阳形时获得了自由,又让在仅有的男性力比多所包含的坐标缺失前感到不安。
强迫性神经症假冒这一器官的存在,这将显得非常尴尬,因为它是危险的。如果男人没有实现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从认同父亲到爱父亲的转变(女人则被视为已完成此转变),那么对于他来说,则必须要承担起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忧虑”。当然,这一忧虑联系于一种象征性忧虑,因为没有人曾经割掉阴茎,不过器官的存在应当被考虑进来。遵照临床差异,必须要觉察阉割忧虑并不是阴茎嫉羡的反面,丧失的风险不同于寻找缺失的。对于强迫神经症来说,忧虑是其根本性的模式,在其中呈现出了欲望。不要忘掉这点: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欲望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意识的。作为结果,伴随着一种永久的逃避,尤其是在女人方面,表现出胆怯性。不过,这是一种复杂的忧虑。
为了理解这点,RSI这三个范畴的定位应当能够使我们理清头绪。
忧虑等同于欲望;弗洛伊德以如下这种形式提出了这个观点:担心父亲死了,或者/且担心女人死了,被解释成希望父亲死亡。这种欲望具有其无意识的特征;鼠人个案可以作为论证这点的范式:在这一个案中,死亡的欲望,也就是说忧虑,惊人地因父亲已经死亡而被双倍化。因此,死亡的愿望和主体与之相关的父亲,即现实的父亲无关。因此,和阉割一样,这种忧虑是象征性的。
那么,后面该如何防止这一忧虑呢?正是在此处,旨在“避免担忧的事物发生”的预感介入进来,各种仪式都起着相同的作用。信念支配着这一行动,因此所谓的强迫症状自然属于想象界。它是一种保护措施,旨在避免“忧虑”切入前的恐惧。
那么,至于实在界呢?对于这点,必须要牵扯到性的维度以及作为享乐的身体的影响。最清楚不过的是这一场景:鼠人的自慰被父亲幻觉性地进入门口所打断。禁止表现为父亲对享乐的禁止。
对于怀疑,时常存在一个不被理解的关键元素。强迫症的怀疑不在于徘徊于两种方案之间,而是拒绝承认已被决定的或已采取的方案。于是,“预感”进入这种动力学中。这种预感是作为“不选择”的解决方案,因为选择已经完成了。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尽管它想要是自由的。
这些例子都是非常常见的,可以在生命的各个行动中,尤其是爱情行动中得到证实。情境的每次转变,比如和一位女士安定下来、结婚、接受生孩子,还有有了一个情人,离开情人,庆祝纪念日,等等,均是出现这些临界点的时机,在其中仪式将替代不可能的选择。我要重复的是,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已经完成了。拉康所说的“不可能的欲望”正是这个意思。分析能够衡量这整个想象性的杂乱思想——这些杂乱思想是对立于承认已被执行的选择。因此,担忧女人死亡或希望她死亡直接联系于欲望以及女性享乐。对于这点,服从于一个女人的欲望代表着承担阉割的勇气,在其中,男人们的剧烈反应(目前人们经常谈到这个主题)是一种胆怯的结果;根据“欲望是关于大他者的欲望”这一公式,其所胆怯的正是顺从欲望。“遵照象征性路线”的行动假定要通过大他者的欲望,在这里指得是遵照女人的欲望。
一个特别简单且常见的例子是一旦生了孩子,就不再有性关系了。一个成为母亲的女人,即自此之后被禁止作为女人,是一种虽然平淡无奇却又并不必然错误的解释。事实上,它得了证实。还有,必须要在每个个案中沿着蜿蜒曲折的象征关系,因为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的缘由,而非一种武断的解释。
如此一来,强迫症的分析将从想象的躲避走向支配他的象征秩序;在这样的方式中,实在才有可能被抓住,被理解。
当然,如果癔症性维度占上风的话,我们同样能够举出女性这一方面的例子。与前者(强迫症)一样,同样的情境也极为常见,我们可以就同一方面来谈谈。比如,一个成为母亲的女人拒绝做“已成为父亲的丈夫”的女人。这时,孩子成了阴茎的等价物,通过这一解决方案,她今后用不着阴茎了。于是,象征性的等价物使得症状重新出来,因为它配得上这个称呼,即便抱怨可能不会很明显——这次轮到丈夫抱怨。当然,还有其他的抱怨可以替代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解决方式,一旦一个女人接受或拒绝进入游戏,以解剖学的名义,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实在——她从不曾有过这一器官。这个实在从阴茎嫉羡型阳形问题中引出享乐,只要这个实在被适宜地理解成大他者欲望的界限而非其竞争因素。
正如大家已经注意到的,通过以主体的性别来处理神经症主体的临床,我有些忽视了这个事实:即主体的位置并不必然符合解剖学所规定的性别属性。我想提及精神分析所不断强调的身体的存在,因为好像由于象征界的排他性(专利权),弗洛伊德式的冲动或拉康式的享乐已被人们遗忘了。不过,身体的物质性是关键性的,可因这点而得到证实:即在男人那里器官的存在对癔症来说构成了一个障碍;因为在癔症那里,女人缺失这个器官并不妨碍她可能像一个男人那样进行阳形性活动,且有时表现出强迫症。